中国网:呈现|“寻家”之路 道阻且长(No.103)
Posted on May 10, 2015 by Agustinus Wibowo in Interviews, 中文 // 0 Comments
印尼人?中国人?从18岁起,奥古斯丁开始只身踏上“寻家”之路,当行走成为挑战自我的模式,他的足迹开始踏及吉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遍布整个中东。终于,他通过行走得到了内心的和解,打破了旧有的“墙”,让当下和过去握手言和。
An in-depth article from China.com.cn (中国网) on my searching of identity as a Chinese Indonesian, about my winding journey to find the real “home”.

印尼华人作家奥古斯丁最近把自己微信签名改为“新书要出啦”。34岁,十余年旅途,行走阿富汗、巴基斯坦、外蒙古等地。按他话说,《Ground Zero》作为他第三本书甚至凝聚他30年行走心血,一切视角核心围绕“家”。“对,我就是想给大家讲一个回家的故事”。
“寻家”因于他曾分不清自己是哪里人,印尼人?华人?这种自我身份无法认同的过程驱动他踏上寻家之旅。如今,他用文字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路上寻家的过程。
实际上,印尼,中国,印尼华人,两片土地,以及在这上面生活肇始非同源的人们,从上上个世纪开始曾为生存而共存或斗争,更多沦为政治纠葛而罅隙,周遭山河变,转眼一切让在新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开始尝试和自己内心和解,用时光消融曾经的伤或痛。
奥古斯丁行走世界,虽漫笔各地域,落笔终回归印尼和华人的人与事,字里字外尝试解读这个新世界。

无“根”可寻的后人
在伦敦书展之前,奥古斯丁的行走版图未曾踏过欧洲,这次借参加书展第一次来伦敦,书展的规模让他略显震惊,但他不在意这个城市的繁华和发达,“我刚才在路上在看哪些流浪汉,他们没有家”。
自始至终,他都在关注自己一直在寻找的“家”的概念。甚至在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他也能很快代入作家角色,娴熟介绍自己书中想要寻求的答案。
其实对于欧洲他并不陌生。早年,他的印尼籍堂兄弟们有的选择欧洲作为逃离印尼的第二故乡,也有些去了澳洲或美国。动荡的印尼政治时局是这种逃离的直接因素,“那时候的印尼不是我们的家,印尼华人在全世界找自己的栖息所”,这种所指可追溯到奥古斯丁的父辈,甚至祖父,以及曾祖父辈。
19世纪,作为第一批印尼华人,成为当地大户人家后的曾祖父回到中国,看中了善良能干的福建小伙,将他从福建带到印尼和自己唯一的女儿成亲,这个人就是后来奥古斯丁祖父。1948年,他们的孩子,奥古斯丁的父亲出生,后被送进当地的华人学校接受教育。时值印尼局势和中国保持一致,政党分两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共产党占主流,父辈受毛泽东影响极深。因华人只占印尼当地人口4%,人少力单,教育形式则统一采用普通话教学。
祖父只会讲福建话,父亲接受普通话教育。在高中二年级中文学校被迫关闭,父亲就此经商谋生,仅会少许爪哇语。到1981年出生的奥古斯丁,再次进入华人学校,所学中文更是少之又少。“无法和父母沟通,更别提和祖父母他们交流了,所以我们无法从长辈那里知道更多关于中国的事。”
两个种族在一片土地上共存,虽为利益有过罅隙,然而二战期间,中国女人不能被带往印尼,于是和当地人联姻结盟开始成为一种融合方式,以对抗特殊社会制度下的生存。而这种极具生存哲学的社会行为产生的附加值便是越来越多的中华元素被稀释。
奥古斯丁自身更有体会。表兄弟中开始出现蓝眼睛的后代,越来越多的亚裔孩子们不会说中文,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是哪里人。
近百年历史沉浮,贯穿印尼华人祖孙辈的情感羁绊,因语言障碍,因联姻,情感在一步步萎缩。而这种情感的纽带更消逝于对曾经源起华人“根”的断代。
“你要问我三代以上的祖辈,我说不上来,我们根本没什么家族谱,祖先牌位之类东西,唯一保留的就是老照片”,奥古斯丁偶尔也觉得,因为语言文化,中国这个故乡是一个让他“只能看到他在哪里,但是却看不懂”的地方,他们是“lost generation”(失去的一代)。

An old Wakhani women smilling happily about her good wheat harvest.
期待的故土
估计是好奇心太重了,伴随着这点滴残缺记忆,奥古斯丁被撩拨了内心中原始的求知欲,开始渴望知道更多长辈口中这个“根”的故事。
而大多数印尼华人对于中国的全部印象皆自一代代口耳相传下来模糊记忆,更多源于想象,“且所有记忆也仅停留当初第一批移民华人离开中国时的样子。”
“当初对中国所有印象和概念都是一片片”,后来真正来到中国生活,奥古斯丁可以很精确对比当初对这种印象的差异,“所以,印尼华人当初对于自己的’根’只是一个国家的概念,没有那个省市村,就是中国,地图上的那个版块”。
他清晰记得8岁那年,生于印尼,终生未去过中国的外婆,有天对着一幅中国地图边哭边说,“我们原来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海棠叶啊,现在就是一个鸡的形状了。”
当时他确实记住了这么一个叫中国的地方。在遥远的地方,有我们很早的祖先,但是那个地方具体在哪里?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不知道。
中国的记忆还包括妈妈给他们兄弟讲的《西游记》里的故事,也是爸爸妈妈在家里曾经唱起的“青藏高原”,还是每天广播里响起的“Radio Peking”。
被无限遐想的美好,也来自于当初那个动荡的环境。80年代始,印尼特殊的政治环境,让生活其中的华人生活状态一直很不稳定。
华人不能参加任何印尼政府事务,“为了生存,你需要挣钱,买一份’安全感’”。然而从商带来的经济条件优渥,使得印尼当地人和华人沦为政治利益的工具,激化纠葛而罅隙。尽管,几乎每户印尼华人家中都雇佣5个以上本地人作为佣人,华人上街出门也时常遭当地人袭击。
8岁奥古斯丁会小心翼翼的保护自己的中国名字“翁鸿鸣”,只允许家人在家里叫,更绝对不能让学校当地同学知道,“因为这都会成为被同学嘲笑的导火索”。
历史课上老师讲印尼历史溯源,点名问奥古斯丁,“你是哪里人?”“我想,我说你们语言,我用你们名字,我生活在这里,我是印尼人。老师说,不对,你是中国人。”
放学后同学围在他周围,大声叫他中国“新客”。小奥古斯丁哭着跑回家跟妈妈说,妈妈一句带过,“你本来就是这里新来的客人啊,你有什么好难过的。“奥古斯丁当时并不能理解母亲这种自我解嘲的心态,“现在想想,没有这种心态在当时你怎么活”。
伴随着整个70-80年代苏哈托极权时代的“排华运动”,印尼华人境遇每况愈下。由于政府排华没收当地华人店铺,奥古斯丁家未能幸免。店面被政府关闭,择日强行出售。父亲和当地百余人华人结盟,前往政府进行抗议,于是被诬陷为共产党。参加抗议的百余人皆被政府关押入狱,一年有余。
种种,越是被压抑,越发加深当时华人内心无限放大对中国的信仰。于是,“能回中国是当时所有印尼华人的梦想”。
为此,他成为家族中这一代唯一一个学中文的后人,就像从小妈妈就跟他说,你要回中国,回中国,那里是你的家。
彼时,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迷失的家园
18岁,奥古斯丁在父亲鼓励下回中国去寻“根”。
“我要回家了”,带着一种无比兴奋感,2000年,奥古斯丁只身前往北京清华大学学习。然而,当带着记忆中“一片片中国”抵达北京,身置清华园,他发现,他是大家眼里的“印尼人”。
“我虽和他们外形一样,但我在这里是作为国际学生在这里学习,我住留学生公寓,我付国际生学费。”作为一个不被认可的中国人,这种困境让奥古斯丁深觉失落。
同时另一种现实让奥古斯丁体验到自己认为的这个“家”的残酷:曾经在印尼每次考试全市第一的学生,来到清华第一次考高数,全班倒数第二。
一度,因从小生活动荡环境下的恐惧感开始再次侵蚀奥古斯丁,“以前在印尼,出家门100米我们都会做人力三轮车,因为路上就有抢劫,外面很危险”,学习的压力把这种恐惧感延续。
“清华压力大,那段日子我想过自杀”。但如当初所有在印尼生存的华人的信念一样:你一定要拼命,否则你无法生存。
不过,奥古斯丁开始接受这环境,除了学习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成绩开始有起色。毕业时,成绩比本地学生平均绩点还要高。但他知道,这一切不是他想要的。
同样对现实中国产生心理落差感的还有奥古斯丁的母亲。
2005年奥古斯丁大学毕业,母亲满怀期待和兴奋来北京参加儿子毕业典礼。到毛主席纪念堂,母亲虔诚瞻仰,每到一处宫殿,母亲认真叩拜,“她那么认真,却看到其他游客仅仅把这些地方当作旅游景点,拍照留恋”,对中国的幻想与现实碰撞的落差让母亲倍感恐惧。
“这完全不是她小时候被灌输的中国的样子”。奥古斯丁了解这种感觉,在印尼,无论历史如何沉浮,当地华人都极度保护自己的“华人身份”,且不谈是否门第为商贾世家,小门小户平时行事为人也皆谈吐有度,基本礼仪道数皆悉数遵守有佳,“在印尼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我们骨子里觉得自己尊贵,惯常言行也要求严格自律。”
奥古斯丁认为,从他18岁离开印尼前往北京开始大学生活,这是他概念中的第一次“失去家”。大学期间的中国生活,让他在毕业后依旧在想,“哪里是我家?”直至后来留京工作,奥古斯丁觉得中国没有带给他这种感受。
此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印尼人。于中国,他“是个外人”。

家是路上的放逐
但可惜的是,历经各种身份被否定,他还是无法排解曾经生活带给他的恐惧阴影。
“我要寻找恐惧感的解脱”。直面恐惧才能解决内心的恐惧。这事儿,在2002年大学暑假的外蒙古之行,他似乎找到了这感觉。
“那次,我刚到外蒙古,不会语言,不知道当地环境,第一天钱包被偷,第二天再次遭遇抢劫。当时我走在路上忽然被三个彪形大汉围住。我顿时吓的闭上眼睛,心中就一个念头,完了,这下一切都完了!过了一会儿,忽然发现,哎,怎么没有动静了,睁眼一看,原来周围有几个警察过来了!我竟然没事儿!“一口气松下来。”
如今再次说起那次经历,奥古斯丁语气轻松,“我想这个时刻我都经历了,我还有什么好怕的,还有什么危机我不能面对的。”
如果说这种内心的蜕变来自这种旅程,奥古斯丁的变化也让父亲对他印象也产生巨大改观,以前那个只会躲在房间里看书,看邮票的“可怜虫”终于开始敢出门了,甚至开始一个人出门当背包客了。
这种认同的鼓舞是巨大的。他举例到,2003年非典过后,中国国门打开,奥古斯丁又一个人跑到阿富汗,“我在喀布尔网吧里给爸妈发邮件,跟他们说我在清华园读书。”
行走开始成为似有似无成为奥古斯丁挑战自我的模式,他的足迹开始踏及吉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遍布整个中东。
作为一个背包客,依靠一本70年代旅游手册,在巴基斯坦一路搭顺风车,一住六个月;在阿富汗作摄影记者,边走边工作,一呆三年,“我开始爱上在这种未知状态中探索,或许会有一种更大的恐惧呢,我似乎就是在跟自己的这个恐惧的内心在争斗。”
开始父母并不反对这种行走。五年、六年过去后,母亲开始问,“你什么时候停下来啊?”
“我觉得我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理想”,奥古斯丁总是这样回答。
奥古斯丁开始四海为家,每到一处都入住在本地人家里,尝试融入当地人生活。而翻看奥古斯丁行走路途中拍摄的照片,每张人物肖像都绽放无邪纯真的笑容:无论在被认为战火纷扬的阿富汗,还是巴基斯坦或者被认为落后的中东某偏僻村落。
“照片是内心的照应”,奥古斯丁笑,并非刻意捕捉,他觉得他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这份纯真的“归属感”。就像他在书里写的,“这里是他在寻找的天堂”。

内心的和解
这种行走纪录的状态甚至开始成为他和父母沟通最独特的方式。他将行走的经历变成文字,并供稿印尼最大报纸“冒险者”,开辟专栏。父亲要母亲第一时间把儿子的文章打印出来,编辑发稿晚了,父亲都会着急。“我不能陪伴父母身边,我只能用这种方式跟他们分享我的故事”。
“现在停下来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恐惧”,奥古斯丁低头片刻,所以当2007年目前得知母亲生病,决定回家,“哪个时候对我真的是个很难的决定”。
2009年母亲癌症晚期,奥古斯丁停下脚步,陪伴母亲前往深圳住院治疗,两个月。“那段时间和母亲度过最难忘的一段日子,也让我重新认识母亲。”
病魔无亲。2010年7月30号,奥古斯丁母亲离世。2013年1月28日,这第三本书刚印出来之日,父亲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
“那一刻我就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生活目标“,而双亲的离去,也让奥古斯丁开始重新思考命运,开始尝试和这个世界,和自己的过去,甚至是之前排斥的东西和解,和自己内心和解。
和解,不仅仅是某个体的幡然顿悟,更是一座城,一个时代的反思和民族的新融合。打破旧有的“墙”,让当下和过去握手言和。
现时的印尼,往昔动荡不再,国家城市的繁华早已被另一种记忆取代:印尼华人依旧遵循着中国传统的春节拜年活动,却改“拜”为基督式的握手方式;印尼华人的婚礼仪式,“看起来尤其像500年前中国传统的婚庆”…
从宗教,外表装扮,到吃喝生活习惯的异化,印尼新一代华人在这片新土地上裹挟着另一种纠结情愫,延续“祖宗”的身份,尤其随着长者的渐次离世而异化为另一重新“印尼式中国传统”。奥古斯丁说,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混杂”。
”过去我定义印尼加华人这两种身份是’互为敌人’,但是现在,它们开始共存,都是我身上的色彩,而这种色彩也让我可以承担更多责任让这两种文化更好的融合。
从曾经小我的”恐惧感“中蜕变,到现在,奥古斯丁开始从更深的层面思考整个一代的印尼华人的生活状态,他翻译余华的《活着》,时代虽不同,“但这本书里描述的情节和我这一代印尼华人当时经历的生活状态极其相似。”
他将继续讲自己行走的故事,并翻译给不同国家的读者,“我希望我的书中的经历可以让读者有些触动和改变。”他还会继续行走,下一步前往印尼周边村落,探索印尼边缘文化,“书写,分享经历。”
“现在你找到想要的家了吗?”
奥古斯丁指着自己心口位置。
“如果具象到一个地方呢?”
“应该是印尼吧,因为我所有的身份证明文件上都写着我的国籍是印尼。”奥古斯丁一字一顿的说。
记者后记
见面两次,两次通话,越来越多的交谈,甚至闲谈,漫谈,接触中让我越发觉得奥古斯丁并非仅仅是这次“回家”之旅的一面。他偶尔有点诡邪的小动作和假动作让我觉得,这是一个走世界,懂生存之道的男人。因为行走本身就是一个人成长的一种磨砺和对周身的锤炼。同时,他身上似乎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平静和淡漠,这种东西超然外物,且绝不能忽略。他言语不谈物质,更多聊及精神层面,这点吸引人。娓娓道来一个故事,信手拈来一个煽情的人生感悟。从这个层面看,他是个很棒的写作者。但是,我更愿意去了解他作为一个凡夫俗子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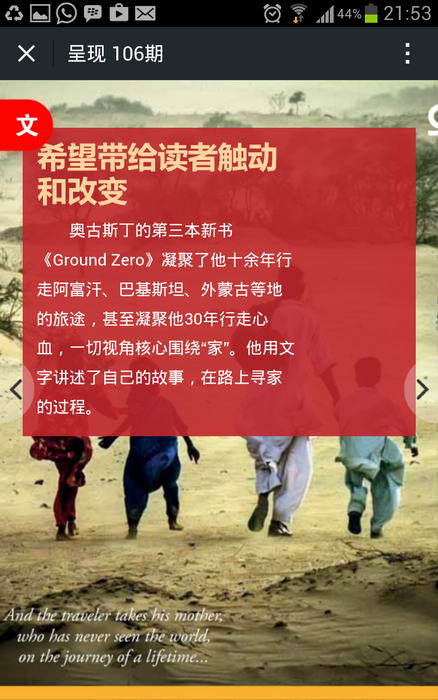






Leave a comment